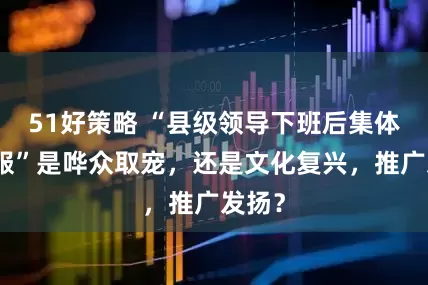
当某县几位领导干部下班后身着宽袍广袖的汉服,或漫步古城墙、或参与非遗手作的照片在社交平台流传时,舆论迅速分裂为两大阵营:支持者称赞这是 “用身体力行激活传统文化”,批评者则直指其 “借汉服搞政绩作秀”。这场争议远超个人服饰选择的范畴 —— 作为基层公共权力的代表,县级领导的 “汉服行为” 本质是 “权力与文化的公共展演”,其背后折射的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中文化建设的路径困惑:当公共权力介入传统文化推广时,如何区分 “真诚的文化实践” 与 “功利的符号造势”?又该如何界定权力在文化复兴中的角色边界?
一、现象解构:权力身份与文化符号的叠加效应在社会学视野中,“县级领导穿汉服” 绝非单纯的 “私人文化表达”,而是带有鲜明公共属性的社会行为 —— 领导干部的身份特殊性,使得 “下班后” 这一私人时间维度的行为,仍被公众纳入 “公共权力运作” 的认知框架。根据布迪厄的 “文化资本理论”,汉服作为传统文化符号,本身具有 “象征资本” 属性;而领导干部的权力身份,则赋予这一符号额外的 “政治资本”。两种资本的叠加,让普通的服饰选择演变为一场 “看得见的文化治理”。
展开剩余86%这种叠加效应首先体现在 “公私领域的模糊化”。传统认知中,“下班后” 属于私人领域,个人可自由选择文化表达形式;但县级领导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参与者,其身份具有 “全天候公共性”—— 公众会自然将其私人行为与地方治理导向关联。例如,若该县正推进 “文旅融合” 政绩项目,领导穿汉服的行为就极易被解读为 “项目宣传的配套动作”;若当地并无系统性文化建设规划,这种孤立的汉服展示,则更可能被视为 “无实质内容的哗众取宠”。2023 年某县 “县长直播穿汉服卖特产” 事件之所以获得认可,正是因为汉服展示与地方产业推广形成了闭环;而部分地区 “领导偶然穿汉服拍照” 引发争议,恰是因为缺乏与公共事务的关联性,导致符号与实质脱节。
其次,这种行为还暗含 “文化权威的建构意图”。领导干部集体穿汉服,本质是试图通过权力背书,将汉服从 “亚文化圈层符号”(如年轻人的汉服社团)提升为 “官方认可的主流文化符号”。这种建构若能结合民间文化需求,可有效打破传统文化的圈层壁垒 —— 比如某县领导穿汉服参与民间端午祭典,带动了当地群众对传统礼仪的参与热情;但若是脱离民间基础的 “单向输出”,则可能形成 “权力主导的文化霸权”,反而消解汉服文化的民间活力。例如,某县曾要求中小学教师集体穿汉服上课,却因未考虑教学实际需求和教师意愿,最终沦为 “形式主义闹剧”。
二、争议背后的社会心态:对 “权力作秀” 的警惕与对 “文化复兴” 的期待舆论对 “领导穿汉服” 的两极评价,本质是公众双重社会心态的投射:一方面,是对基层权力 “形式主义作秀” 的长期警惕;另一方面,是对传统文化复兴的迫切期待。这种矛盾心态,源于近年来基层治理中 “文化政绩化” 现象的负面影响与传统文化 “圈层化生存” 的现实困境。
从 “警惕心态” 的根源来看,公众对 “权力 + 文化” 的组合始终保持审视,源于部分地区此前的 “文化政绩泡沫”。例如,一些县市耗资数亿打造 “汉服小镇”,却因缺乏产业支撑和文化内涵,最终沦为 “空置景区”;有的地方强制要求商户穿汉服营业,忽视商业经营的实际需求 —— 这些案例让公众形成了 “权力介入文化 = 政绩作秀” 的刻板印象。当县级领导集体穿汉服的行为出现时,公众首先会基于 “过往经验” 进行风险预判:若行为缺乏后续文化建设措施,仅停留在 “拍照宣传” 层面,就会被归入 “哗众取宠” 的范畴。这种警惕并非对传统文化的否定,而是对权力滥用文化符号的防御。
从 “期待心态” 的维度来看,公众对汉服的关注,反映了传统文化 “破圈” 的迫切需求。近年来,汉服文化虽在年轻人中兴起,但仍面临 “圈层化” 局限:汉服爱好者多集中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群体,在县域层面的普及度较低;且汉服文化的传播多停留在 “服饰展示” 层面,对其背后的礼仪、历史、工艺等深层内涵挖掘不足。公众期待看到有影响力的主体(如领导干部)推动汉服文化从 “小众爱好” 走向 “大众认知”,从 “服饰符号” 走向 “文化实践”。例如,某县领导穿汉服参与传统纺织技艺传承活动,带动了当地非遗工坊的发展,这种 “符号 + 实质” 的模式就获得了舆论认可 —— 公众期待的不是权力对文化的 “掌控”,而是权力对文化的 “赋能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,不同群体的评价差异还反映了文化认知的代际分化。年轻群体(尤其是汉服爱好者)更易接受领导穿汉服的行为,因为他们将其视为 “传统文化获得官方认可” 的积极信号;而中老年群体则更关注行为的 “务实性”,若不能直接带动民生改善(如促进文旅就业、提升文化教育水平),就可能被认为 “不务正业”。这种代际差异,本质是对 “文化价值” 的不同定义:年轻人更看重文化的 “身份认同价值”,中老年人更看重文化的 “社会实用价值”。
三、文化复兴的真伪检验:从 “符号展演” 到 “实质建构”判断 “县级领导穿汉服” 是哗众取宠还是文化复兴,关键不在于 “穿汉服” 这一行为本身,而在于是否构建了 “符号 — 实践 — 价值” 的完整文化链条。真正的文化复兴,绝非表层的服饰展示,而是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现代转化,以及对公共文化生活的深度参与;若仅停留在 “拍照宣传” 的符号层面,则必然陷入 “哗众取宠” 的争议。
(1)检验标准一:是否与民间文化需求形成互动
传统文化复兴的核心动力源于民间,权力的角色应是 “引导者” 而非 “主导者”。若县级领导穿汉服的行为,是对当地民间文化需求的回应,而非单向的 “政绩展示”,则具备文化复兴的基础。例如,某县民间汉服社团长期面临活动场地不足、资金短缺的问题,领导穿汉服参与社团活动,并推动政府提供公共文化空间支持,这种 “权力呼应民间” 的模式,让汉服从 “领导符号” 转化为 “群众文化载体”;反之,若当地并无汉服文化基础,领导却强行组织 “集体穿汉服”,则可能导致 “政府热、群众冷” 的尴尬局面,沦为形式主义。
(2)检验标准二:是否构建长效文化建设机制
短暂的服饰展示无法支撑文化复兴,只有建立长效机制,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落地。例如,某县在领导穿汉服引发关注后,顺势推出 “汉服 + 非遗” 培训项目,邀请民间艺人教授传统刺绣、礼仪知识;建立 “汉服文化研学基地”,结合当地历史遗迹开发文化旅游线路;将传统礼仪教育纳入中小学课外实践 —— 这些措施让 “穿汉服” 从一次性事件,转化为持续的文化建设行动。反观部分地区,领导穿汉服拍照后并无后续动作,汉服仅成为宣传海报上的 “道具”,这种 “一阵风” 式的行为,自然被视为哗众取宠。
(3)检验标准三:是否避免文化符号的 “异化使用”
传统文化符号若被过度工具化,可能丧失其本质价值。汉服的核心价值在于承载历史记忆、传递礼仪文化,而非 “政绩宣传的工具”。若县级领导穿汉服的行为,始终围绕 “文化内涵” 展开 —— 如在传统节日中主持祭典,讲解节日习俗;在文化论坛中分享汉服背后的历史故事 —— 则是对文化符号的正向使用;但若是将汉服与 “招商引资”“排名评比” 等政绩目标强行绑定,如 “穿汉服签约项目”“以汉服宣传考核政绩”,则会让文化符号沦为 “权力包装的外衣”,背离文化复兴的初衷。
四、基层治理中的文化理性:权力的角色边界与多元参与“县级领导穿汉服” 的争议,最终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命题:在基层治理中,公共权力应如何参与文化复兴?答案并非 “完全退出” 或 “全面主导”,而是要确立 “有限介入、多元参与” 的理性边界,让权力成为文化复兴的 “赋能者” 而非 “掌控者”。
首先,权力应明确 “引导而非指令” 的角色定位。基层政府的核心职责,是为文化复兴提供公共服务支持,而非直接主导文化形式。例如,制定传统文化保护政策,为民间文化社团提供场地、资金支持;搭建文化交流平台,促进汉服爱好者、非遗传承人、学者的合作;加强文化教育普及,将传统礼仪、历史知识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—— 这些 “后台支持” 远比 “前台穿汉服展示” 更具实质意义。正如某县的实践所示,政府不直接组织 “领导汉服活动”,而是通过补贴民间汉服展演、支持汉服主题文创开发,让文化复兴自然生长,反而获得了更持久的效果。
其次,应构建 “民间主导、多元共治” 的文化治理模式。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民间的自发参与,权力的过度介入可能压抑民间创造力。可借鉴 “协商民主” 的思路,成立由民间文化爱好者、学者、企业代表、政府人员共同组成的 “文化发展委员会”,共同制定当地文化复兴规划 —— 汉服文化的推广形式、内容设计、活动组织,均由委员会协商决定,政府仅负责资源协调与监督。这种模式既能避免 “权力作秀”,又能确保文化复兴符合民间需求,实现 “官民共治” 的良性互动。
最后,需警惕 “文化复兴” 与 “政绩考核” 的过度绑定。基层政府的文化建设应避免 “短期化”“指标化” 倾向,不能将 “汉服活动次数”“文化宣传曝光量” 等表面指标纳入政绩考核,而应关注文化复兴的长期效果 —— 如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提升、民间文化社团的发展活力、文化产业对民生的带动作用。只有打破 “政绩导向” 的束缚,才能让文化复兴回归 “滋养心灵、凝聚认同” 的本质价值。
当县级领导的汉服身影出现在街头时,我们不必急于贴上 “哗众取宠” 或 “文化复兴” 的标签,而应观察其背后的行动逻辑:是短暂的符号展演,还是持续的文化建构?是权力的单向输出,还是官民的共同参与?真正的文化复兴,从来不是少数人的 “表演”,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 “参与”—— 当汉服从领导的照片里走进普通人的生活,从服饰展示走向文化实践,从县域角落走向大众视野时,文化复兴的种子才算真正落地生根。这,或许是 “县级领导穿汉服” 争议带给我们的最珍贵启示。
发布于:上海市配资炒股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